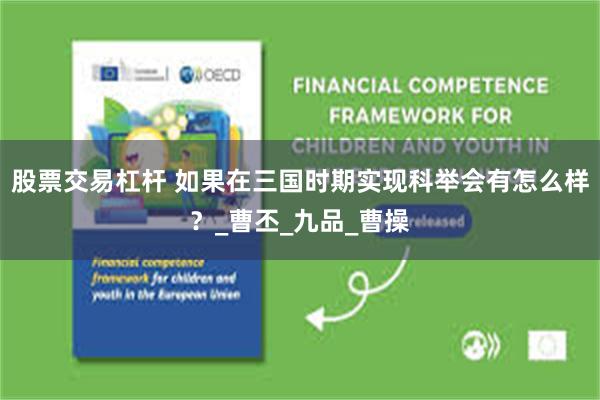
士族和九品中正是三国迷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股票交易杠杆,但由于掌握资料有限,加上一些早期研究的误导,常常令有关这方面的言论陷入似是而非的境地。比较典型的如著名同人mod游戏《姜维传》里就提出用科举制替代九品中正制的想法,那么这样的想法真的现实吗?
研究历史首先需要摒除的两种思路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和跳跃式的断层发展。放到九品中正制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把九品中正和科举看作是水火不容的两样事物,其实并非如此。九品中正由察举制衍生而来,科举则是由课试制发展而来,两者都是由汉武帝所创制,之后长期都是并存的。创制九品中正的曹丕也创制了五经课试,学通经典便可以凭其入仕。因此两者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谁更占据上风。
同时,九品中正也不是一个凭空而来的制度,而是应时而产生的。九品中正制的正式颁布是在曹丕时期,但一些资料中则显示曹操时期就有了九品中正制的雏形,而近年考古发现中正的名称早在初平年间(190-193)就已经出现。中正最初可能是各郡国自行认定的当地善于品鉴人才的人,且并不是正式的官职,而是民间推选,由郡国认定其资格。这种方式经过曹操时期的发展,最后在曹丕时期正式成形,并成为制度。因此中正制是承袭自东汉以来士人中喜好品评人物的风气,这股风气又诞生于察举制的实行以及儒学的大盛时期。而到了东汉末年,士人颠沛流离,乡人之间可能出现互不相识的现象,这就更加迫切需要一个明确的标准以及权威人士来对人才进行判定,这些因素联合起来促使了九品中正制的诞生。唯有认识到这些,才能了解九品中正制的诞生背景和历史意义,知道这是一个有历史渊源的制度,而不是曹丕和陈群哥俩互拍脑门,突发奇想创造出来的。
展开剩余87%对于九品中正制的很多误解接下来将逐一解释。
首先不少人将这一制度理解为曹丕出卖特权给大族,借以换取士族的支持。这一论断由唐长孺等历史学家所提出,影响了许多人。但这样的早期观点实际上已经被不少学者所驳斥,并拿出了相关证据,即使在原始史料当中,也从来没有将二者画上等号。首先汉魏时期是否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士族阶层目前在学界尚有一定争议,通常认为这一时期只是士族的萌芽期,而一个九品中正制能立竿见影地让士人跑来支持曹丕更是有些让人匪夷所思,毕竟一种制度要看到成效是需要时间的,而曹丕在继位的当年就完成了禅代。
其次,九品中正制的走歪是有一个过程的,在南朝的沈约在《宋书·恩幸传序》中就写道,九品中正制推行的初衷是为了区分人才的优劣,而非给大族们排一个座次。因为是顺应时势而产生的,这一制度实行以来自然是有不少问题,比如夏侯玄在正始年间就提出改革九品中正制,但他的着眼点在于中正和吏部并行,造成了人才选拔标准的混乱,而非士族对官位的垄断。而垄断仕途的问题真正显现已经是司马炎统一三国之后,尚书令卫瓘和尚书左仆射刘毅一同上疏司马炎时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在奏章里写出了那句著名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然而此时曹丕都已经去世快六十年了。此外,卫瓘和刘毅都认为九品中正制是基于当时特殊背景而制定的权宜之策,并非长久之计,这应当是符合事实的,至于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居然贯穿了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历史,这多多少少有点出乎当时人们的意料。
而在九品中正制的发展当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司马懿设立大中正一职。大中正是州级的中正官,负责一个州的品级评判。这一做法在当时就被一些人所反对,例如曹爽的弟弟曹羲,道理很简单,一个州太大,大中正怎么可能清楚这个州的所有人才孰优孰劣,最后的结果还不是大中正按个人的意思随意确定等级。司马懿确立大中正的意思也许是为了加大中央在等级判定中的话语权,毕竟郡国评判人才有着很强的乡邻风习。但当时正好又是大族崛起和曹魏开国功臣二代迅速成长的时期,这些权贵凭借大中正一职迅速把持了人事任命。而在晋王朝渡江后为了站稳脚,出让权力和大族合作,皇权进一步衰落,大族们几乎垄断了仕途,这才令九品中正制真正成为大族的工具,如果说曹丕、陈群开国时就能料到这些,而当时的大族们也看到了这样的结局因而支持曹丕,那也未免太过料事如神了。
在批判九品中正制的过程中,又常有人将曹操抬出来树立为对立面,例如史学家陈寅恪就称曹操所要建立的是庶族法家政权。然而事实上从秦朝灭亡及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法家就在读书人之中成为了异端学说,最后不得不和儒学融合形成律学而得以存续,法家政权已经失去存在的土壤。且曹魏政权并没有在任何方面表现出对抗政权儒家化的历史趋势,曹操本人虽用法严格,但也拥有较高的儒学修为,不但任用了大量名士,自己在撰写文书时也常常用到儒家经典中的典故。至于经常被拿出来提到的求贤令和“唯才是举”,更多是在汉魏嬗代时期的特殊形势下的政治口号,“唯才是举”并不包含任何强制命令和可操作的指标。最重要的是,前面已经提到,九品中正制的雏形就是在曹操时期形成的。
在指出这些错误的认识之后,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强行在三国时期实行科举制会是什么情况。
在看待历史问题时,一定不要有我比古人聪明的想法。穿越文里容易出现类似主人公穿越到古代,然后运用现代人的知识烹制出蛋糕、火锅、炒菜等美味的现代美食,之后成为神厨的故事。然而真的穿越回去所要面临的现实是,宋朝之前因为技术限制造不出铁锅,辣椒等一系列植物要等到明朝末年才传到中国,古今动植物品种有差异口感也不同等等...所以如果客观条件达不到,那么再巧妙的想法也难以实现,古人所缺乏的往往不是想法,而是环境。
在科举制的施行所需要的条件里,首先所要面对的是考生来源的问题。需要了解的是,科举制的出现也不是马上就消灭了士族,与很多人的印象不同,士族这一群体在唐朝依然很活跃。唐朝时的科举取士以进士和明经两科为主,所选用的人才非常有限。以进士为例,唐朝一次科举考试所招收的进士在全国只有二三十人,有的年份甚至一个考中的都没有。而且科举所选取的士人在地位上也远不及那些靠家族恩荫出仕的高官子弟,科举制度实行初期,三品以上的大员几乎全部被高官子弟所垄断。也就是说,唐朝的科举制只是给士族以外的子弟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另外这一时期的科举还禁止工商从业者参加。到了宋朝时宋太祖才大幅度增加科举取士人数,但直到南宋时期,科举取士做官人数仍远不及靠家族恩荫入仕做官的人数。
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数量本身就不多。全民识字在整个世界都只有很短的时间,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绝大多数群众都是不识字的,根据清朝末年朝廷统计,当时全国识字率不到1%。即使认为清政府的统计方式不够科学,数字不准确,这个比例也绝然达不到10%。很多人因为秀才是科举制度下最初级考试的合格者,便并不将其放在眼里,还有了穷酸秀才一词,然而清朝末年全国拥有秀才以上功名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甚至比今天的大学教授还低。大家熟悉的《范进中举》故事里,范进考了几十年的科举终于考上了举人,他的成绩是广东省第七名,而广东省现在每年就会产生四十多位市文理状元,还需注意的是,范进考的科举是三年才举行一次,因而举人的数量远低于现在的市高考状元。
既然如此,那说明范进读书非常厉害吗?是也不是。范进能中举那他确实有一定的过人之处,但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教育资源严重稀缺,在那九成九不识字的人里,天资超过范进绝对不在少数,如果让他们和范进经过同样的学习再去参考,范进是绝然无法再考上这个名次的。同时,由于古代的学校教育制度不完善,尤其是科举制度兴起后官学形同虚设,科举考试里考生的教育开销必须由考生自己全额负担。对于平民而言,这是一笔沉重的开销,而且会随着社会越安定、教育水平越高、考试竞争越激烈而越发昂贵。此外,光是参加考试就需要付出大量金钱,据统计,明朝末年一位考生参加完全套的科举考试,花在旅费、食宿费、小费、礼品费、宴会费、交际费这方面上的数额大约是六百两,远比今天的学生去美国留学昂贵,完全不是普通家庭能承担得起的。像范进这样的普通百姓孤注一掷地苦读一生,最后翻身跃龙门的实在少之又少,无怪乎其当场发疯。
为什么当时不大力兴办教育,提高民众识字率呢?很简单,直接原因是兴办教育需要的成本开销太高,政府难以承担,即使是新中国也是在建国37年后的1986年才颁布《义务教育法》,确立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制度,而全部免除义务阶段学杂费则是要等到2006年,教育这一块的支出对于封建王朝来说过于高昂。而根本原因则是农业社会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分子,少部分人用来维持社会和政府的正常运作,多数人都去种地才是农业社会的合理结构,不然教育出一大堆知识分子要怎么去安置?
而教育的扩大化也是一种历史趋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观念的进步,受教育群体在不断向下发展。知识分子在先秦时期主要诞生于贵族士大夫阶层,汉魏晋时期产生了高门大姓,由此出现了士族阶层,经过南北朝的演变,寒族又开始崛起,最终凭借着唐朝的科举制以及五代十国的乱世,寒族渐渐取代了士族。这里要解释的是,寒族或者说寒门这个群体和现代人的理解是不同的,寒门并不是指普通民众。寒门这个词汇里,寒是形容词,门才是主体,普通民众是没门的。士族指的是门阀制度下的高级豪族,而寒族则是次级豪族,类比到今天的话,士族起码是省部级以上的家庭出身,而市委书记的家庭则毫无疑问是寒族。例如晋书里提到周访和陶侃二人是寒族出身,周访的祖父官至威远将军,父亲官至左中郎将,陶侃的父亲官至扬武将军,这差不多算是当时标准的寒门家庭。
宋朝之后,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科举考试的扩大化加上印刷术的推广应用,平民中开始产生一些知识分子,这才有了评书戏曲小说等一系列市民文化生活体裁的作品。但真正让全民都具备一定受教育水平,还是得靠新中国成立后的扫盲运动和九年义务教育,这些都是离我们不远的事。而教育扩大化的趋势依然在推进当中,继全面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国家又在研究十二年义务教育的可行性。
把时间移回到曹丕所处的汉魏之际,此时的教育普及程度远比清朝低,而且由于印刷术尚未发明,书籍成本也远高于后世。《诸葛亮集》里就有提到诸葛亮曾为刘禅抄写各类书籍,诸葛亮贵为丞相,他亲自抄写书籍体现了对刘禅学业的关心,但也反映出即使当时的高门权贵想要看书也得靠抄写。西晋的左思写出《三都赋》之后,人人争相传抄,便有了洛阳纸贵一词,当时传抄《三都赋》自然也是洛阳的文人和权贵们,而非平民。汉魏晋时期的文化世家都有家传一经的传统,就是为儒家经典做注,然后作为传家宝代代相传,其中不乏高门大族。可以说像关羽这种熟读《春秋左传》的人,在文化层次上已经直接和普通民众拉开了差距。
如果在这个时候实行科举制,由于教育资源的严重失衡,可以想见到时候这种考试必然被世家大族所垄断,平民几乎不可能在众多世家大族的包围下突出重围。举个很近的例子,建国后曾一度废除高考,其一大原因就是教育资源过于倾斜到城市,导致高考几乎被城里人所垄断,得不到同等教育资源的农村人对高考制度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对于汉魏当时来说,教育资源失衡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大力兴办教育制造平民知识分子的不可行我在上文已有提及,因而在生产力、技术和社会观念使教育扩大到士族以下群体之前,科举制对普通人会是比察举制更加不公平的制度。比如说汉末京兆人鲍出和酒泉人杨丰分别因营救母亲和见义勇为,被州府征辟为官,但如果是在科举制度下,靠读书他俩能有这个机会吗?
同时科举如果在汉魏时期实行,还要考虑许多实际操作层面上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考题怎么出。如果要用科举替代察举或者中正,那么科举考试里的考题就要代表国家的正统思想。但汉魏时期读书人之间并没有能够统一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儒家学派受到严重打击,西汉初年儒学发展缓慢,即使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其他各学派依然存在了一段时间。东汉时经学得到了重大发展,但大家对于儒学经典的研究并不像后世那么透彻,学问终究是要拿来实践操作的,孔孟二圣也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面面俱到地写进来,读书人之间的意见往往并不统一,因而面对不同的问题时各家便有了不同的解释,就出现了各个分支学派。例如西晋初年官方以司马昭老丈人王肃的学说为官方正统,但很多读书人并不买账,民间仍是郑、王、马三家学说并行,甚至官方也不断吸纳郑玄的学说与王肃的相结合。
更重要的是东汉末年时局动荡,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之前几十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以前的说法和做法拿到当时是未必行得通的。关于守孝,郑玄就提倡守够时间,而且各项要求要严格执行,但当时的社会环境很难有这个条件,实行起来就有困难。而过了几十年后,社会渐渐安定下来,大家又有这个条件了,面对这样的变化,要怎么确定执行标准?另外,不同的社会环境又会产生大量前人所没有经历过的新问题,例如战乱导致了许多家庭的离散,男性二娶和女性二嫁都是当时常见的现象,那么面对父母家庭重组后的另一方及其子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儒家先圣没有专门去研究这种问题,儒学者们也会有大量争论。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即使朝廷出台一套思想标准,也未必得到读书人的认可,这就加大了实行科举的难度。
总而言之,任何制度有其诞生的条件和背景,九品中正制也是如此,这套制度顺应了当时的特殊背景并发挥过一定作用,但并非长远之计,且因为种种原因而迅速变味成为了大族垄断仕途的工作。如果当初在卫瓘和刘毅的提议下将其废除,后来的历史大概又会是一种不同的光景。而科举作为更加公平合理的制度也是顺应了寒族崛起的条件而诞生的,如果不顾环境强行将其搬到汉末,那势必遭到现实的阻拦而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和在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社会搞资本主义一个道理,两者都是难以实现的。
最后重申观点:
一、九品中正制有其诞生的特殊背景,说它单纯是曹丕用来讨好大族的工具有失公允,其在一定的时间里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二、汉魏时期尚不具备实行科举制的条件股票交易杠杆,此时强行实行科举制难以达到预想中的效果,更不可能一跃进入大唐盛世。
发布于:天津市